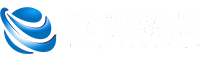“我的基本結論就是,它搞‘亞洲北約’,或是北約擴大到亞洲,實際上是它虛弱的表現,它一個人自己擔當不起。”
 【資料圖】
【資料圖】
“中美發生世紀博弈的根本原因,問題還是在美國不能接受中國崛起。”
在東方衛視6月26日播出的《這就是中國》第191期節目中,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院長張維為教授和中國人民大學金燦榮教授,剖析中美關系的新特點。
金燦榮:
中美關系最近變化挺快、挺復雜,我覺得它有一種矛盾性。一方面我們可以看到某些緩和,比如6月18-19日,美國國務卿訪問中國,這是五年來美國國務卿首次訪華,也是拜登執政兩年多,他的“正部級干部”第一次來,所以也是好事。稍早前,5月23日,謝鋒先生赴任中國駐美大使,在此之前差不多近五個月時間,我們的駐美大使是空缺的,這個情況其實是不太正常的。隨著謝鋒大使到任,這個環節就比較正常了.
另外,5月25-26日,中國商務部部長王文濤到美國開APEC貿易部長會議,見了美國商務部長雷蒙多、美國貿易代表戴琪。6月5日,美國國務院亞太事務助理國務卿康達到訪中國,主要是跟中國外交部美大司司長楊濤會見,也見到了外交部副部長馬朝旭。
此外,大家也注意到了拜登本人的表態,很想跟習主席見面;接著,拜登總統的國家安全事務助理杰克·沙利文也明確表示,希望安排兩國元首會晤。
這是中美關系的一個方面,但另一方面形勢又很嚴峻。在布林肯訪華之前,美國又是以各種理由制裁中國企業,包括“新疆強迫勞動”,再者是美國的軍機、軍艦不斷闖入我國的有關區域,軍機是闖入解放軍在南海的一個演習區,軍艦是穿過臺灣海峽,被蘇州艦逼著改了航道。這個美國有點不習慣。
與此同時,香格里拉峰會在新加坡舉行,中美兩國防長沒有正式會談;中國國防部長李尚福見了日本防相、韓國國防部長,但沒有見美國國防部長奧斯汀。
所以,我的理解就是中美關系現在挺矛盾,雖然有一些緩和,但我的判斷是這個緩和是技術性的、戰術性的,而不是結構性的、戰略性的。它的目標其實是負面的,比如布林肯來華,是防止中美關系“螺旋式下降”,但大的結構,從戰略角度、結構角度來講,中美關系就進入到了世紀博弈,這將是一個很長期的博弈。
中美發生世紀博弈的根本原因,問題還是在于美國不能接受中國崛起。我覺得現在美國有兩大戰略判斷錯誤。第一,它從種族主義角度來講,不能接受中國崛起,它認為你是非白種人,你怎么能崛起?你怎么有資格崛起?大家經常引用一段話,就是美國前總統奧巴馬在澳大利亞講的,“如果中國人都過上我們美國這樣的生活,那是地球的災難”,這是種族主義,意思就是你沒有資格享受跟我一樣的生活。這是違反普遍人權原則的,,背后反映的是種族傲慢,社會達爾文主義、霸權主義心態。
6月19日下午,國家主席習近平在人民大會堂會見來訪的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圖自新華社
第二,它覺得自己有能力阻止中國崛起,這個判斷肯定是不對的。所以這兩個問題導致中美關系出現了根本矛盾。
我們可以試著把根本矛盾化解為具體矛盾,現在中美關系性質變了,從既競爭又合作轉向了競爭為主,那么具體有哪些方面的矛盾呢?我歸類為五對矛盾:
第一個身份矛盾。美國是西方的領袖,而西方是現存國際秩序的既得利益集團,它作為最大的既得利益集團的頭,自我定位就是現狀維護者。中國是正在發展,而這個發展確實在改變現狀,現在很多西方引以為傲的東西都被我們拿下了,中國走在世界前列,新興產業也正在追上來。所以美國就把我們定義為“修正主義國家”,什么意思?就是你改變了我領導的秩序,所以你是“修正主義國家”。這是一對身份矛盾,美國自認是“現狀維護者”,把我們當成“現狀改變者”。
第二個矛盾就是我們經常講的力量對比矛盾,老大和老二的矛盾。美國是公認的老大,我們中國也認;美國認定我們是老二,國際關系里面把老大和老二的矛盾叫做“修昔底德陷阱”。請注意,美國很擅長整老二,第一個整的就是英國,六親不認,下手挺狠,通過提出“民族自決”概念,鼓動各地鬧獨立,把英帝國給肢解了,接著整德國,再然后整蘇聯,但蘇聯因為有核武器,它不敢真打,弄了軟性力量,煽動蘇聯內部變革,培養了很多“兩面人”,最終成功了。現在網民管這個叫“遠程畜牧業”。美國的“遠程畜牧業”特別發達。再接著是日本和歐盟,所以在我們之前美國已經整趴下五個老二了,現在它要開始整我們了。
這個東西回避不了,不是說我們低個頭、讓點利就能解決的。面對這種情況的辦法就是發展,好好地發展,提升綜合國力,不僅GDP要超過它,綜合國力也要超過它,人民生活水平要趕上去,通過發展逼它承認我們的崛起,才可以解決這對矛盾。
第三個就是比較顯見的矛盾,政治制度的矛盾。我們堅持黨的領導,它要我們搞多黨制,想要顛覆我黨的領導,這是一個明顯矛盾。
第四個是文明矛盾,這個稍顯復雜,所以我多說兩句。美國是西方文明集大成者,西方文明有一大特點是一神教,信教程度很高。在美國普通民眾當中有一套邏輯,這套邏輯在我看來是很蠢的,但是它管用,那就是大部分美國老百姓真的堅定不移地相信他們的上帝是最偉大的,他的上帝要壓倒對方。中國說我們可以交朋友,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有和平共處的思路。但他們是沒有的的,就覺得自己的上帝最偉大,然后說上帝最喜歡我,為什么我這200年混得好,就是因為上帝喜歡我,我是上帝的選民,理所當然我應該領導世界,就是這樣一套邏輯過來的。但現在他們有點集體困惑了,因為他們的領導層跟美國人講,說中國崛起了,而且威脅到美國了,這讓他遇到了一個邏輯問題:中國人不信上帝,上帝都不認識你,你怎么混得比我好?這不科學。于是,全民陷入一種焦慮困惑,接著就開始打我們,有了文明矛盾。
中國人信的是規律,不信上帝;我們從古代拜的“天地君親師”,“天地”就是自然規律,“君親師”就是社會規律。所以美國人無法理解我們,因為兩個文明體系不一樣,而他們的心態又不對,對一個東西感到陌生,他不去主動了解,產生了邏輯矛盾,很焦慮,人一焦慮脾氣就不好,就打我們。
第五個是種族矛盾,這一點美國人不怎么提,但實際上是非常深刻的。不知大家注意到沒有,崔天凱大使在美國擔任了八年大使,回國以后他就說他覺得到美國的種族主義是大麻煩,因為種族主義從生理、心理上無法接受我們的崛起。我們必須承認過去幾百年確實西方干得很好,這是事實,而西方主體又是白人,于是就有了白人種族主義優越感,對黃種人、黑種人、棕色人種是看不起的,說直白一點,是把我們當下等人了。這就導致當我們在崛起時,他們從生理、心理無法接受。這其實是五對矛盾里面最難解決的。怎么辦?還是前面講的我們要好好發展。
以去年10月拜登政府的《國家安全戰略報告》為標志,美國已經單方面發起了對華新冷戰,不是中美新冷戰,證據是它的政策跟冷戰時期的對蘇政策有四個共同點:
第一,確立一個全球對手,那時是蘇聯,今天就是中國,報告里面講了中國現在是唯一既有能力又有意圖挑戰當前秩序的國家。第二,就是內外動員。現在美國內部的反華已經意識形態化了,只要批評中國肯定是正確的,在家里辦事辦得不順都怪中國,比如債務到了天花板了——現在已經過了32萬億(美元),差一點就要違約,財長耶倫怎么說服國會兩黨?她說這個事不能干,否則中國人要笑話我們的。增加軍費、科技投入、教育投入,都以中國說事,把反華意識形態化,借此動員社會,這是對內。外部也進行了動員,比如在亞洲,美國正在搞“亞太小北約”,特點就是讓日韓和解,促進美澳合作,通常是美日韓三家再帶著菲律賓搞演習。此外,還有“北約亞太化”,要很多國家選邊站,這是外部動員。
第三是全方位施壓。現在美國有一個全政府對華政策,就是各部門不許自行其是,對中國的壓力不能留空隙,于是乎有了貿易戰、產業戰、科技戰、司法戰、輿論戰,搞軍事威懾,等等。將中國定位為對手,內外動員、施壓,但第四點又提出不能打熱戰,因為打熱戰就不是冷戰了,美國肯定要付出很大代價,所以它要整你,但會控制一定邊界。
所以,根據上述邏輯,我個人認為,美國單方面的對華新冷戰開始了,但中美新冷戰沒有開始,為什么?第一,截止到今天,中國不應戰;第二,戰略上我們沒有搞集團對抗,不像蘇聯,我們沒有要求任何國家站隊;第三,我們不搞軍備競賽,現在我們的外部環境很差,但軍費增長跟其他各方面的支出增長相比其實不是很快,我們主要還是發展經濟發展。
另一點是,就算到現在我講話的時候,美國的內外動員并不順,首先內部動員,美國企業家還是不配合,4月份蘋果CEO庫克來了,6月份馬斯克、比爾·蓋茨、星巴克老板等,來了一堆人,中國市場還是很有魅力的,所以企業家不太配合。習主席見了比爾·蓋茨,提到寄希望于美國人民。所以我們現在的對美工作是雙管齊下,政府能對話就對話,民間能交流就交流,就是因為看到美國內部有些人其實不愿意,企業、有些地方政府、民間團體不愿意,這樣我們就有了工作的空間。再者,外部其實也沒有動員起來,老歐洲就不干。馬克龍公開表態,北約是管北大西洋的,亞太跟我沒什么關系,他反對北約亞太化。新歐洲,像匈牙利肯定也不參加。還有些西方國家,像以色列、新西蘭,大概率也不會參與。還有一個很關鍵的是第三世界國家,就是所謂的全球南方國家都反對新冷戰選邊。
這就是我看到的中美關系的情況,結構上來看不樂觀,未來還是很嚴峻的。那么怎么辦?我覺得主要還是幾方面,中國肯定主觀上特別重視中美關系,因為我們知道中美關系的好壞決定人類命運,決定著我們星球的命運。習主席提了很好的三原則,中美關系必須相互尊重、和平共處、互利共贏。那么,我們的處理方法就是不激化矛盾,現在問題主要還是在美國方面。
美國是這樣的,拜登當局作為當家人,想搞平衡,于是提了一個3C對華政策,就是競爭、合作、對抗。首先這個政策本身是矛盾的,另一個麻煩是美國政局太多元化、派系特別多,而拜登控制不了,這就不確定了。
最后的出路,其實前面已經提過,發展,取決于中國的發展。中國要認真搞發展,一是國力要上去,另一個是發展成果一定要普及民眾,最終體現在人民生活水平好起來。這樣一來,從宏觀到微觀都在改進。我估計到了一定階段,美國還是可以改變態度,接受我們。
我的分享到這里,謝謝大家!
中國海軍“蘇州艦”攔截美軍“鐘云號” 視頻截圖
【圓桌討論】
主持人:金老師對中美關系當下的情況,特別是美國國內的情況,做了一個非常透徹的分析。金老師在演講中說到一個觀點,其實美國的戰略戰術能力是非常強的。科技戰、貿易戰、認知戰等等各種戰,密不透風。大家可能知道新冷戰是怎么回事,從中可以看得出它的戰略戰術能力,但可惜的是戰略出現重大誤判,所以能力再強,只會讓它在錯誤的方向上走得越遠。張老師您也可以給我們做個分析,這次布林肯訪華,怎么解讀這個戰術動作?
張維為:我覺得這次蠻有意思的,首先是很多細節,比方說,雙方商定他來訪問,不是應邀。你不是我們邀請,正式邀請,是你自己想來,我們商量一下定個日子。然后,那就來吧。
另外是習主席見他的時候,坐法的安排跟過去不一樣了,照網民的解讀,就是開始要給他上課了。但你仔細看一下,央視放的那段視頻里面,習主席的表情非常嚴肅,我估計可能不亞于當時跟馮德萊恩說的“癡心妄想”。
總體上,我一直比金老師稍微樂觀一點兒,我們講中美關系一定要經過交鋒才能達到更好的交流,從“否認”到“憤怒”,到“部分接受與討價還價”,到“接受”四個階段,我覺得現在經過交鋒,有一點兒開始進入“部分接受”了。經過交鋒之后,貿易戰徹底失敗,不是一般的失敗,95%的增加的稅都是美國消費者支付的,科技戰也在失敗邊緣,然后是軍事上,你看這次我們蘇州艦在臺灣海峽橫刀立馬,就是叫你改變方向,叫你降速。還有前面提到的我們在南海對美國偵查機采取的行動,用殲-16戰斗機的尾氣使它震動,這是很厲害的,要稍微用多點力氣,飛機要360度旋轉的。以我對我們中國人民解放軍的了解,做這樣的動作就是給你立規矩。
美國希望什么呢?它希望擦槍但不走火,所以要各種各樣的所謂“護欄”措施,但看這次會談的報道,大家注意到沒有,我看美方的報道他們感到失望,因為軍方的溝通沒有重新建立,我們沒有同意。雖然美方說我們恢復了雙方高層的接觸、溝通,但是軍隊之間沒有,也就是說我們軍隊的立場放在這里:你想擦槍不走火,我們告訴你擦槍可能就要走火,你要做好準備。我想我們一定是做好準備的,我們是做任何事情都是有底線思維的,如果蘇州艦去了,萬一碰撞了怎么辦?發生了沖突怎么辦?甚至炮擊了怎么辦?打沉了怎么辦?我相信我們一定有一個安排,關鍵是讓美國人知道你是有安排的,就是我根本不害怕你,這是最關鍵的,這使他看到,他不得不趕快來談,要盡快地建立各種溝通渠道,來防止雙方關系惡化。其實我們也不希望惡化,我們這樣做也是為了防止關系惡化。所以這次雙方有一個重要的共識,就是雙方都希望“穩定中美關系”。
主持人:就像美國遏制中國發展,這是它的戰略方向,戰術上有很多做法,它抵近偵查,但你不要有反應,希望擦槍,但不能走火,我們稍微有點反應,它認為你不專業,在它的字典里什么叫專業?所謂的專業就是我可以侵犯你,但你不能有任何還手,這個叫美國式的專業。這背后的核心就是霸權思維。這段時間來,美國跟中國的關系,它越來越體會到霸權思維和霸權做法踢到鋼板,剛才金老師在演講里說它已經搞掉了五個老二,以往積累了無數成功的經驗,但那些成功經驗突然間不是那么成功了,這個它也需要適應。
金燦榮:現在我覺得美國在摸索,它也會與時俱進,目前為止我覺得他沒找到。有美國負責人講,中國好像跟以前的范例都不一樣,歐盟很松散,中國是完全統一的,然后像日本、德國、英國雖然經濟效率都不錯,但規模小;俄羅斯是規模大,但經濟效率差;而中國是又大、經濟效率又好、然后又團結。
目前我覺得美國還在摸索,那要怎么讓它接受呢?我其實完全同意維為教授講的可能需要斗爭,一味地順從、退讓是不行的,斗一斗,反倒把規矩給立起來了。中國現在主要是工業化,中國反復強調現代文明是工業文明,工業是基礎,尤其是制造業,而這一塊中國已經贏了。
我們回顧一下,那五個被美國整趴下的老二都有一個特點,就是制造業都不如美國,單一國家最高都沒有達到美國70%,歐盟作為一個總體,制造業達到過美國的85%,但中國是多少呢?去年2022年,中國的制造業總產值是美國的196%,基本上是兩倍。這相當于美國、日本、德國、韓國和意大利之和,今年很有可能超過G7,這是中國很厲害的地方。但很多人還沒有注意到、包括美國都沒有注意到,但是它們真正的專家是知道的。美國現在有點過度政治化,結果是很多專家靠邊站,然后出來一批很怪的政治家,這就影響他決策的質量了。
2020年7月,中國宣布制裁四名美國政客,從左至右分別為布朗巴克、克魯茲、盧比奧和史密斯。
主持人:其實這些都談不上是政治家,就是民粹的政客,他只要高呼反華口號,就可以有選票,這是美國選票政治走到極端之后,非常悲哀的地方。張老師一直有一個觀點,中國自己就是一個世界,這么大的國土,這么多的資源,這么多不同板塊的發展,特別是我們現在說人民對美好生活日益增長的需求跟發展不平衡、不充分之間的矛盾,乍一看它是不足,但仔細看全是我們的增長點,從這個角度來說,我們的騰挪空間比那些國家大得多。
張維為:我一直是看好中國模式,看衰美國模式。美國模式資本為大,以資本為中心。那這兩個模式的發展的路徑和效果就不一樣了,西方讀不懂中國模式。
金燦榮:這個也正常,因為人的認識能力很有限,所以肯定是現象到本質,目前就是現象上它開始承認你的崛起,而且不是完全承認,還在學習當中,否則它怎么會傻乎乎地去搞貿易戰呢?貿易戰就是它在發起的時候肯定覺得會贏,結果它已經輸了貿易戰,科技戰大概率也是輸的,產業戰大概率也是輸的,所以這些現象他都很難承認,何談本質呢?它需要有個過程,這個過程中的關鍵還是中國要發展好。
張維為:實際上我有個基本的判斷,就是總體上世界從2008年金融危機之后,進入了“后美國時代”,這不是說美國不重要,美國還是很重要,但美國的思想、想法不再代表未來的方向,大家都覺得,都看得很清楚,你是有問題的。
然后很重要的一點,中國是一個“文明型國家”,它真的有很多很多智慧,我們當時為什么分析特朗普的貿易戰肯定要輸,我們第一時間做節目就說貿易戰肯定要失敗的,我們分析美國的決策過程,你哪怕是跟你們美國的企業的代表做個協商,初步了解一下,但他們是先宣布要制裁,先宣布要征稅,然后再去問企業去,結果企業一片反對聲,95%的美國企業都反對。我就說是你的決策過程反了,你要學習我們的“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這個民主集中制的決策過程,我們決策慎重得多,也靠譜得多。
主持人:金老師演講里頭說了一個詞,叫規律,就是按照規律辦事,比按照想象辦事,那要有效果得多。我覺得中國可能連普通老百姓都知道規律這兩個字的力量,再加上我們還有幾千年的文化傳統積淀下來的許許多多的智慧。
張維為:我們講到規律,實際上用現代詞匯也可以叫“底層邏輯”。你看,為什么美國從內部、外部動員來反對中國,結果都不那么成功。我們可以先聚焦外部動員,它的底層邏輯就是我經常講地緣邏輯,整個歐亞板塊——中國、俄羅斯是兩個這個板塊的中央,這是完整的超大型的國家,都是“文明型國家”,有長久、悠久的歷史文明;然后在這個板塊的兩頭,一個是歐洲,二十多個國家,分裂的,這個結構決定了它很難完整地整合起來;亞洲這一頭也類似,韓國、日本、菲律賓等,也是一個破碎的板塊,所以從地緣結構上來講,它要整合起來是非常困難的。美國,包括其盟國全部拼湊起來,要針對中國,結構上看,不大可能成功。
所以我的基本結論就是,美國搞“亞洲北約”或者是北約擴大到亞洲,實際上是它虛弱的表現,它一個國家擔當不起,它對付不了你,然后湊幾個,湊一批,但參與的各個國家都有自己的算盤、自己的心事。
金燦榮:我好像在這個節目說過,戰略研究是四個層次,道、法、力、術。道也就是循規律而為,規律就是道,就是你不要違背規律,循道而為。法是利用你的優勢,把這個優勢用法律形式固定下來,這樣管理成本就比較低。力,就是憑蠻力了。術,就是一些小技巧。
我的觀察是,二戰以后中國基本循道而為的,什么階段該做什么事,做得挺好。現在是強起來,該做強起來的事。美國是“法”做得比較好,充分利用自己的優勢,把它變成普遍規則,讓人家接受。俄羅斯是典型的“力“,他們自己也承認,俄羅斯沒戰略,俄羅斯戰略就是蠻力;遇到阻力,鐵棒橫掃,阻力加大,鐵棒加粗。日本是“術”,老搞些小動作。但現在我又得出一個新結論,好像美國有點往術那里走了,搞小動作。所以,習主席說大國要有大國的樣子。
中國現在提倡人類命運共同體,發展倡議、安全倡議、文明倡議,在戰略層面,大家好像在拉開,美國現在還有點資本,但按照現在這種玩法,越來越小氣了。
【提問環節】
觀眾:兩位老師好,主持人好。我叫黎國成,來自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想請教一下兩位老師,如何看待經濟發展不及預期下的中美關系,謝謝。
張維為:實際上經濟是這樣的,我老講一切在于國際比較,現在權威的國際機構,你可以列出三四個,對中國今年的經濟預期增長為5.5%左右,還有更高的,也有稍微低一點的,5.5左右,美國是0.5%左右,他們都是對中國比對美國樂觀。你仔細再看看,華爾街的代表,美國大企業的代表,大企業的CEO,都到中國來,他們都更看好中國經濟。
金燦榮:經濟我不懂,我只是用常識看,現在很多信息說明我們中國經濟確實是比較困難。主要是民營企業家信心不足,他不愿意投資,我們就遇到了困難,供給沒有問題,主要消費側有問題。所以我們首先得承認困難。
但是因為它涉及中美關系,我覺得美國也沒有理由樂觀,剛才張教授講了,我們是比以前慢一點,但美國更慢了。中國經濟有困難,這對我們肯定有強大牽制,但就中美關系而言,目前這個經濟困難好像沒有改變的總的態勢。總態勢就是中國發展還是快一些,中美力量還是在接近。
張維為:我們前面已經提了,因為整體上西方都面臨不同類型的危機,像美國面臨嚴重的通貨膨脹,四十年來最嚴重的,你看這么多次地采取了包括加息等各種手段,但也只能把通脹大約從9%降到6%,這還是很高的通貨膨脹。
有時候我就覺得一切在于比較,之前在藍廳論壇,我就講了,世界幾乎所有國家,包括美國,都經歷了幾種危機中間的至少一種,比方說銀行危機、糧食危機、能源危機、其他危機,像歐洲還有難民危機,中國全沒有經歷過,我們沒有經歷通貨膨脹,我們沒有經歷銀行危機,沒有經歷能源危機等,,這已經是很了不得的成就。如果你說中國都沒有機會,那全世界都沒有機會了,真是沒法比的,真是這么回事情。
金燦榮:上個星期李強總理在出訪之前開會,就是談怎么解決年輕人就業困難,這個是事實,政府也在想辦法,我覺得民間也有些力量在想辦法。但還是剛才張老師講的情況,國際比較來講,我們機會還是多,所以美國企業的頭部大佬,像埃隆·馬斯克,像比爾·蓋茨,眼光還是可以的,他們從比較角度看,這里機會還是多,他是來找機會的,就全球而言,我們的相對優勢還是有的。
6月14日,比爾·蓋茨訪華。
觀眾:兩位老師好,我來自中國香港。,畢業于清華大學蘇世民書院,研究國際關系。隨著中東地區和解潮的加速,中國在其中發揮著非常重要的作用,同時也積極在推動中東和解跟和平發展。您認為國際社會對于中國接下來的一些行動或者決策有什么期待?同時在另一邊,美國在中東地區的影響力是否在減弱?美國可能會有什么反應,或者戰略調整?這樣的一種變化對于中美關系會有什么樣的影響?謝謝。
張維為:我認為,美國是想搞破壞的,但現在能夠動用的手段比過去要少一些。我們這次真是了不起,沙特、伊朗能夠在中國斡旋下恢復外交關系。美國在中東主要是兩個抓手,一個是以色列,也就是利用以色列和阿拉伯世界、和伊斯蘭世界的矛盾,對以色列全方位支持。
另外就是把伊朗豎成一個靶子,讓大家圍攻伊朗,但現在伊朗、沙特和解以后,它就犯難了。今天的伊朗和沙特都相當成熟,他們的資深的官員相當成熟,這個太重要了,他們不愿意再上你美國當了,但對于阿以的矛盾,美國肯定還要挑,就是以色列跟伊斯蘭世界的矛盾。
金燦榮:咱們中國外交到了強起來的階段了,每個發展階段任務肯定不同,在強起來階段,中國就有必要給世界做貢獻,其中一個貢獻當然是和平了,因為和平是發展前提。
我記得好多年前,中國社會科學院老院長馬洪去英國訪問,然后就問英國為什么近代發展這么好。第一英國內戰之后,也就是光榮革命以后內部從來不打仗,要打就到外面打,;第二就是基礎設施要好,第三就是穩定可預期的政策,這是經濟發展的三大前提。
過去我覺得英美爭奪世界霸權有一個“訣竅”,學術一點講叫“離岸平衡”,用老百姓的話就是挑撥離間。大家都聽說過國際關系有個理論叫地緣政治理論,本來你們倆關系還湊合,稍微有點矛盾,但它一定要把你們倆搞得你死我活,這個時候它就有機會了。所以它一定要充分地制造矛盾,這是它介入的前提。
但現在中國的思路是要化解矛盾,促進3月10日沙伊和解,是一個良好的起點,但要達到很好的效果仍需時間,也需要我們綜合國力的上升,甚至還需要人才。我們在正確的路上,任重而道遠。
關鍵詞:
責任編輯:Rex_02